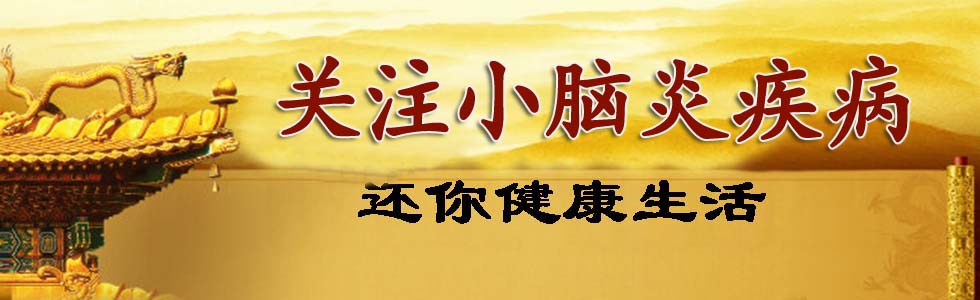
李白写在兖州的“桑蚕诗”
唐代兖州,为东鲁首府,应无争议,自不赘言。李白从天宝十载移家东鲁后,居家兖州。在李白居家东鲁的20年里,据徐叶翎先生考证,写在东鲁的诗有60多首。在上述诗中,细检写东鲁桑蚕丝织的诗作有6首,分别是《赠从弟冽》、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》、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、《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》、《寄远.其十》、《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》。李白在这些桑蚕丝织诗中,写到了唐代兖州季节上的春、夏、秋,写到了唐代兖州的自然景象和生产生活景象,为我们品味唐代兖州,提供了一道鲜活的小菜,从中还可以看出唐代兖州与古丝绸之路的联系,捡回这些细小的历史碎片,细细地把玩,别有风趣。
李白在在《赠从弟冽》中写道:
及此桑叶绿
春蚕起中闺
日出布谷鸣
田家拥锄犁。
这是李白写东鲁春景,桑田生机勃勃,一望碧绿,村姑伺候的蚕宝宝,孵化出壳,正待饲养。清晨布谷鸣叫,农家挥锄或赶着耕牛梨田。写到了东鲁春天的早晨,写到了春之桑蚕。
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》中写:
五月梅始黄,
蚕凋桑柘空。
鲁人重织作,
机杼鸣帘栊。
梅黄蚕凋的季节,鲁人重视织作,可以看出织丝制绢,已是兖州人重要的劳动内容。“机杼鸣帘栊”更是一片繁忙的万家丝织景象。写到了夏之桑蚕及丝织。
在《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》中写道:
月出鲁城东
明如天上雪
鲁女惊莎鸡
鸣机应秋节。
更是写反映了鲁女秋夜丝织的场景,只是在季节上比“梅始黄”的五月晚了些。诗人在这月明如雪的秋夜,细心体察到了鲁女的织机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,惊动了清秋之夜鸣叫的蟋蟀。可以想见勤劳的鲁女在安顿好老人、哄睡幼儿,收拾家务,夜间又加班生产屡屡催货的丝织品,辛劳而又幸福。初夏到仲秋,从季节上,由此更加说明了兖州植桑养蚕是唐代兖州人民的生产重要内容。
在《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》中写道:
送别枯桑下,
凋叶半落空。
我行懵道远,
尔独知天风。
李白在唐代瑕丘城北的曲腰桑树下送别张姓朋友。可以想见,那棵曲腰的老桑树,不知其树龄,历经风霜,弯腰而又倔强生长,已然是鲁城北的一处标志性风景。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兖州的植桑的情况。在季节上,可以看出这是“叶凋半落空”的秋天。《寄远.其十》中:
鲁缟如玉霜
笔题月支书
寄书白鹦鹉
西海慰离居
行数虽不多
字字有委屈。
天末如见之,
开缄泪相续。
千里若在眼
万里若在心。
相思千万里,
一书值千金。
在鲁地生产的丝绸上写月支文,遥寄远在安陆的许氏夫人真切感人,催人泪下。
李白在另一首诗中也写到了兖州的丝织品。
《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》:
鲁缟白如烟,
五缣不成束。
临行赠贫交
一尺重山岳。
鲁缟,春秋时期沿袭下来的产品作为礼品,在唐代的交往中,极为普遍的物质。
刘长史升迁临别李白送鲁缟,虽谦称其不成礼仪,但可以看出,鲁缟仍是日常礼品。
李白东鲁桑蚕丝织诗中所表现出的东鲁风物,写到了兖州的与桑蚕丝织有关春、夏、秋,是一副生动的田园画,展示了唐代兖州大地上的桑麻葱茏之景。
而这块桑麻之地却紧紧联系着世界,西域商队的驼铃,响在古驿道上。
李白《沙丘城下寄杜甫》诗中的“何时石门路”的石门,即横跨泗河的金口坝,连接着西去帝京长安东达海边的古驿道,金口坝东边曲阜的一个村庄至今名字叫古路沟。古路成沟,是千年岁月的雕刻,村名是历史的遗响。
商品的纽带带动着经济的发展,同时进行着文化的交流。山东大地就是这样和世界互动着。而且这种互动从汉代就开始了。
山东的丝绸东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往朝鲜、日本等东南亚国家,西则运往西京长安,经过西亚到达欧洲。
兖州的桑蚕丝织生产,历史悠久,《尚书.禹贡》记载详实,九州物产,兖列其首。地处黄河下游,气候温和,土质咸宜,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特别适宜植桑养蚕。土地气候条件奠定兖州桑蚕丝织经济发达的基础。
在这个基础之上,形成了植桑育麻的传统,桑麻经济的发展,必然催生人才的产生和技术的积累。使其成为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的生产、生活方式。正其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丝织品,乃为古九州之一的兖州的贡品。
“济河为兖州,九河既道,雷夏既泽,雍沮会同,桑土既蚕,是降丘宅土,厥贡漆丝,厥篚织文,浮于济漯,达于海河。”(《尚书.禹贡》)。“邹鲁滨、洙泗,颇有桑麻之业。”(《史记.货殖列传》)。
《兖州府志.人物志八》记载,春秋战国时期“鲁秋胡戏妻”的故事即发生在这里。秋胡妻墓就在兖州城北,东南大社沈罗村(即今漕河乡蔡桥村),附近还有一个村叫罗店村,据传说,罗敷女就是此村的姑娘。
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,商贸的发达市场的需求是促进兖州桑蚕丝织发展的必要条件。自然条件和市场的需要必然催生桑蚕丝织的繁荣。
兖州养蚕的历史有确切证明的时期为春秋时期。年兖州县大安区李家村一古墓中,发掘出土一枚铜蚕。
蚕体长8厘米,胸围3.7厘米,全身首尾九个腹节,胸腹尾各脚完整,制作精致,造型逼真,体态为栖眠状。专家鉴定,为春秋时期产物。由此证明,兖州地区春秋时期植桑养蚕已成生产常态。桑蚕发达可见一斑。
《春秋左传》记载:成公二年—楚侵鲁,鲁贿之以执斫、执针、执紝皆百人。就是说:鲁国送给楚国匠人、裁缝、织丝的奴隶各一百人。
鲁缟之名,见于多种典籍。《史记》中说:强弩之末力,不能穿鲁缟也。几成成语,言其之薄。鲁缟是春秋时期沿袭下来的产品,白色生绢曰缟。缣,为双根并丝所织粗厚平纹丝织物。
甘肃敦煌发现过写有“任城国亢父缣一匹,幅广二尺二寸,长四丈,重廿四两,值钱双六百一十八”的汉缣。
(汉代的任城国也为兖州所辖)缣与绢、绨、䌷、缦、纨、缟均为平纹织物,其中纨、缟为薄型或超薄型织物,缣和绨则比较厚实。这说明兖州当时生产的丝织品的品种既有薄如纸的鲁缟,又有较为厚实的缣和绨。
兖州建有纪念织神嫘祖的机神庙,是兖州一处重要的丝织工业文物。
建筑为单院三开间的古建筑,原内侍奉这丝织业的鼻祖鹅英的塑像,兖州人称为;机神,意为丝织业的祖神。现为济宁市级重点文保单位。
兖州文化部门最近又发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兖绣”。
“兖绣”的特点是历史悠久,针法、技法复杂多样,题材内容,丰富广泛,虽无法与蜀锦并称,但仍闪耀着兖州古代丝织艺术品的独特光辉。据《兖州丝绸志》等文献记载:汉代兖州盛产镜花绫、双格绫等好多个品种。
出土文物、文献资料和至今兖州的生产方式证明,鲁缟的主产地是兖州。李白的东鲁桑蚕诗也是有力的证明。
唐代诗人杜甫在《忆昔》中写道:
齐纨鲁缟车班班,
男耕女织不相失。
这一组组的劳动场景的描写,令人心动神逸。
兖州的出土文物、文献资料都反映了古代丝织业的发达和辉煌,李白的东鲁桑蚕丝织诗更是从生产生活情境上弥补了细节,真是难能可贵。
李白的东鲁桑蚕丝织诗,以五彩之笔,描绘了唐代兖州的绚丽生产生活画卷。读李白东鲁桑蚕丝织诗,仿佛梦回大唐,置身其中,心旷神怡。感谢太白,为我们留下大唐“影象”,使我们能够在多年后感受大唐的诗意情怀。感谢江油这片钟灵毓秀的山水,孕育李白这位天才的诗仙,将东鲁兖州唐代桑麻之景,永恒地载入了人类的记忆。
(注:缣 双根并丝所织粗厚平纹丝织物。甘肃敦煌发现过写有“任城国亢父缣一匹,幅广二尺二寸,长四丈,重廿四两,值钱六百一十八”的汉缣。缣与绢、绨、䌷、缦、纨、缟均为平纹织物,其中纨、缟为薄型或超薄型织物,缣和绨则比较厚实。)
武秀,男,年生于山东兖州。曾任兖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兖州市文化局长、济宁市人大代表。30多年在文化战线工作,有万字的文学、戏剧、评论、文史研究、主编的作品出版、发表,多种作品在省市获奖。戏剧《村支书刘运库》获山东省“五个一”工程精品奖;小说《仲秋的早晨》入选《济宁市改革开放30周年文学作品选》;《谈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及其对“李白在兖州”研究的实证》被收入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《李白研究》卷。现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兖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。
国画作品 徐叶翎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